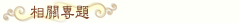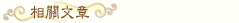(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11月30日訊】 70 生机
從廣播里听到這樣一條消息:在那個冬天的早晨,沈陽市區車水馬龍,成千上万的人騎著自行車去上班。忽然有人發現,在貼近市府大樓的街牆邊,立放著許許多多的花圈,大大小小,參差不齊,看上去有一百多個。這气氛不由人不想起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那年清明節,北京市民以悼念周恩來為由,匯集在天安門廣場,用花圈的海洋向當權者舉行政治示威,盡管招來了血腥的鎮壓,但卻導致了四人幫的覆滅。難道今天在沈陽又出現了什么事嗎?不像。因為這里只有花圈,沒有人。是哪位顯赫人物逝世了?也不像。因為花圈放的不是地方-它們面對的是一排低矮簡陋的平房,好奇的人湊近一看,那花圈上的挽帶上寫著:“關峻山同志千古”,這關峻山是何許人也?一打听,原來他是馬路對面那家小飯鋪的老板-個體戶。昨天晚上,關峻山在一場毆斗中被人用刀子捅死了,送花圈的都是個體戶。
消息不脛而走,頃刻間,成百上千輛自行車在這里停下來。周圍的人擠得水泄不通,花圈還在繼續往這里送。
事件惊動了市政當局,惊動了公安局和新聞單位。有關領導也飛車而至。報社記者也聞訊赶來。
不就是一個普通的個體戶嗎?何故會一“死”激起千層浪呢?听听送花圈者的話吧:“我和關峻山素不相識,但我听說他是個個體戶,就馬上買了個花圈送來。‘兔死狐悲’嘛,動物尚且傷其同類,何況我們自喻万物之靈的人呢!”“我們都是同一個階層的人,生前被人瞧不起,總是低人一等。如果死了也引不起社會的注意,豈不太窩囊了?我們于心不安!”“我們并不想鬧事,只是想讓人們知道我們的存在。我們也在為‘四化’出力啊。”……
這是小事一樁,很快就過去了。但它卻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般說,個體戶就是小商小販。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商品交換就是從個體戶開始的,几千年來,人民群眾的生活一直和小商小販有著千絲万縷的聯系,可以說,他們對人類的貢獻是巨大的。然而在中國大陸,個體戶都有一段曲折的心酸史。早在五十年代,個體經濟作為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五种成份之一,還受到應有的保護和鼓勵〔另外四种成份是國營的、集體的、公私合營的和私營的〕。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逐步深入,國營經濟隨著它的絕對优勢迅猛發展起來。1956年水到渠成,几乎是在一個早晨,全國所有的資本主義工商業一齊敲鑼打鼓“進入社會主義”-相競挂上了“公私合營”的招牌。那些小本小利的“夫妻老板店”,如煙雜店和小飯鋪之類,也相繼改為“代銷點”或“合作商店”。街頭巷尾的小攤販也紛紛納入“合作”的軌道。堅持不走合作道路的少數“頑固分子”,只有落到西風落葉的慘淡景象,奄奄一息了。到了“文革”時期,提出“對資本主義階級全面專政”,要“蕩滌一切舊社會留下來的污泥濁水”,要“割資本主義尾巴”,于是殘留的“個體戶”就成了過街老鼠,一場圍剿和反圍剿的斗爭開始了。讓我們從浙江溫州這“一斑”來看看“全豹”吧。這個地區人多地少,老百姓守這這塊土地“靠天吃飯”是無法糊口的,所有他們世世代代靠做小本生意頤養天年,各种副業如野草叢生,現在要“深化社會主義革命”了,商品經濟就成了“資本主義的溫床”,家庭手工業成了“資本主義尾巴”,小商小販們都扣上“新生資本主義分子”的帽子,這個溫州成了“資本主義复辟的大本營”,這還了得!于是政府采取步步為營的辦法,圍追堵截,務求消滅之。而不甘退出歷史舞台的小商小販們則運用“你追我逃”的游擊戰術,同政府周旋。有戰斗必有傷亡,胜敗乃兵家常事。有一位婦女為生活所迫,東拼西湊弄到一點錢,販了兩簍小蝦,挑到“黑市場”里賣。擔子剛放下,市場管理人員就奔襲而來,其他有經驗的小販早已聞風而逃,她卻束手就擒,兩簍小蝦悉數沒收,全家老小只有去喝西北風。她哭天搶地,求爺爺告奶奶,都沒人理睬,眼看斷了生路,她只好抱恨投河了。幸好被一位過路的老者下水搭救上來,然而那老者卻因耗盡了精力而溺死何中。象這類慘劇是屢見不鮮的。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極左路線結束后,個體經濟又從冬眠狀態中醒過來。政府看到,個體經濟不但在國民經濟中可起調節作用,便利民眾生活,而且可以解決部分就業問題。所以政府一改過去的“圍剿”政策,而為鼓勵和扶持。于是各种各樣的個體戶雨后春筍般出現了。水果攤、飲食攤相繼恢复。在上海,“四大金剛”〔大餅、油條、豆漿、粢飯糕〕也陸續回到街頭來。修鍋的、補鞋的、箍桶的、裝拉鏈的、配鑰匙的、磨剪刀的、包餛飩的,……都挑著他們的小擔,走街串巷,歡樂地吆喝著,微笑著為人民服務,立等可取,效率特高。買賣雙方都眉開眼笑。隨著优質服務,大把大把的鈔票賺進了口袋。所以在城市,“先富起來的”就是這些個體戶。不少人很快成了万元戶。但這些人層次較低,大多文化不高,眼光也不那么遠大。而那些文化較高由有眼光的人就各有千秋了。有的開照相館、音樂茶座,還有的發奮圖強,開創名优產品。安徽蕪湖是全國四大米市之一,一向以大米貿易為大宗,可是解放后實行了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米市不再景气。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安徽蕪湖出了個譽滿全國的個體戶年廣久。他先是在馬路邊擺水果攤,他很會經營,把大小水果分門別類,整整齊齊擺出來,按不同質量標出不同价格,每個水果都揩得干干淨淨,很吸引顧客,因此他的生意很好。然而他的小攤對面是一爿國營水果店,那店里的服務態度水果質量都比不上年廣久的小攤。水果店經理惱羞成怒,就告年廣久“破坏國營商業,挖社會主義牆腳”,年廣久為此被投入監牢!年廣久服刑期滿出獄后,繼續奔,他不再經營水果,而是打起背包到天南海北考察一番,每到一地就買一包瓜子嘗嘗,在全國各地兜了圈之后,回到蕪湖,綜合了各地瓜子的特點,自己獨創了一种瓜子。在此之前,人們說他和國營商店競爭太傻,喊他“傻子”,于是他干脆給自己的瓜子取名“傻子瓜子”,這瓜子一上市就受到廣大市民的歡迎,壓倒了國營的瓜子。年廣久的生意做大了,在全市添了好多個攤位,他發給每個看攤的人以合理的工資。有個看攤人因家中老母生病,他偷偷地從貨款中挪用了二十元,年廣久發覺了,他主動補助那人二十元,告訴他,家中有困難可以補助,不可挪用“公”款。年廣久考慮到每天炒瓜子影響了周圍的鄰居,便主動地貼給周圍每戶人家二十元作為“賠償”,對蕪湖的公益事業,年廣久也積極捐助。年廣久的名聲越來越響,但可惜此人沒有文化,不懂法律,确确實實有些傻,后來竟因偷稅漏稅犯了法于是一個跟斗摔了下來。然而這個個體戶對“活躍社會經濟”所作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個體戶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也不乏其人。上海一個弄堂口設了一個皮匠攤,專門給人們修鞋,這個年輕的小皮匠一天到晚不聲不響地工作,凡過來修鞋的,他只說個价,就接下活儿,認真操作,收錢時,他也不親手接錢,而是讓顧客將錢丟在旁邊的一個筐筐里,如需要找錢,也讓顧客自己動手,小皮匠連看都不看一眼。他受到人們的尊重,那個筐筐里從來沒有“虧損”過。忽然有一天小皮匠沒有出攤,而在攤位的牆壁上貼了一張“請假條”,上面只簡單寫著“皮匠請假兩天”。原來他听說家鄉籌辦一個托儿所,他為托儿所資助一万元人民幣。托儿所開張了,來信請他出席開張典禮。他興沖沖赶回家鄉,在大會上所長請他講話,在熱烈的掌聲中,他登上講台,紅著臉只講了半句話:“託儿所辦起來了,我很高興……”大家想留他參加座談會,他謝辭了,說他很忙沒有時間,就匆匆忙忙赶回上海,在弄堂口“上班”了。
個體經濟就這樣迅速發展起來,除了街頭巷尾的小商小販外,漸漸地擴展出其它行業,在農村辦起了不少磚窯厂、化肥厂、建筑隊,在城市里也有人開了診療所、會計室、照相館、律師事務所以及各式各樣的文化補習班。在上海最著名的便是蔡光天先生辦的“前進”英文學校。蔡先生用高工資聘請了高水平的英文教師教課,學生趨之若騖,該校以高標准嚴要求為原則進行教學,成績卓著。學校發展極快,不但在全市各區辦起了許多學校,甚至后來在美國也辦起了分校。
在個體經濟蓬勃發展的浪潮中,凡是有一技之長的人都可大顯身手了,不少人從“國家”單位辭了職,加入了個體戶的隊伍。上海市共青團的一位領導干部也辭了職而去經營他的小本生意。
我的一位朋友是學藝術的,他也從一家國營工厂辭了職,辦起一個“畫報社”,他熱情地邀請我在業余時間為他“出一臂之力”,這樣我也有了一筆額外收入。此外我還在業余時給人補習語文,也能掙得一份勞動所得。
在這期間,我的儿子也讀完大學,他雄心勃勃地踏進社會。
我的小家庭和整個社會一樣,開始興旺起來。
党中央領導人鄧小平說,可以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于是大家都想“先富起來”,以往几十年的窮日子如同一場惡夢,現在好象醒過來了。
但在党中央,也有人反對鄧小平的“先富政策”,惊呼“不能眼看社會主義江山變顏色”。党內的經濟專家陳云提出個“鳥?F策”,說社會主義好比一個鳥籠,私人經濟好比籠中的鳥,我們可以讓他們任意地飛,但不能讓他們飛出籠子去。
但是這些鳥的命運究竟如何呢?有的因為飛不出籠子而被窒息了,年廣久就是其中之一,我們的“畫報”只出了兩期,因為它的質量太好而被政府視為“有礙國營畫報的發展”而被取締。
那些勇敢的鳥而則仍在不屈不撓地拼命飛,它們誓死沖破這個鳥籠,爭取一個自由飛翔的天空。
本書獲作者授權轉載,欲購者請聯系澳洲羅小姐:[email protected](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