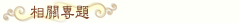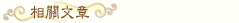暴虐紛沓的腳步順著樓梯跑下去,消防門開著,那足音發出巨大的迴響,聽得出人不少。耳邊的那個聲音依然在怒罵她,有人出手,一下一下地,用巴掌和拳頭打她,都是壯年暴徒,使出的都是十足的力氣,朱錦被打得睜不開眼睛,雙眸閉緊,依然感覺視網膜上一片血光。她被一巴掌搧得跌到一邊,有個站在一旁一直在捶電梯開關的暴徒,看也不看地補了一腳,踢在她的背上,一下子把她整個人踢得順著走廊滑出去。她聽見尾椎骨處發出很清晰的斷裂聲,大理石地板上都是她的血,滑也滑不出太遠。她咬緊牙關緊閉嘴唇,吭也不吭一聲。心裡毫無任何感知,既沒有恐懼,也沒有對暴力的害怕,甚至,很快她就不再感覺到被毆打的疼痛。
走廊裡起初有幾扇門不知死活地打開了一條縫,想看個究竟,見一群壯漢在對一個女子拳打腳踢,都生怕惹禍上身,魂飛魄散地關上了門,還落下了防盜栓。而後,走廊裡靜得好像門背後沒有任何活人。他們把她拖起來,銬上手銬,下電梯直到地庫,扔上警車。她的頭撞到車後面的一個鐵把手上,天旋地轉裡只聽到罵她的那個聲音在接電話,得意樣樣地說了一句,「行了,電梯裡那男的也抓到了。」
「太好了!今晚行動完成。」
「搞笑吧你?在幾個城市搞電視插播,他走得脫嗎?這回就等著死吧!」
朱錦的心往無底洞裡一沉,意念一慌,人便失去了知覺。
她被關進了市公安局的看守所。人頭擁擠的牢房裡,她昏了兩天兩夜,人就在門後邊躺著,從扔進來就沒挪過窩,看上去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屍體,毫無動彈。不知從哪冒出來的一個醫生,在牢房門口看了她一眼,輕描淡寫地說著,人給打成這樣子,拍不拍片子都能看出肯定是有骨頭斷了,腦震盪也有,就看是輕微還是劇烈,這人估計是廢了。
牢房裡和傳說中一樣,骯髒,卑賤,並且人來人往。常常有新人進來,好奇地踢踢她,問旁邊的人,這人是怎麼死在這裡的。也有人腳下不留意,踩到她的長髮上。兩天後,她的意識和肉體在逐漸地、一點點恢復感知。第一念是回憶起被抓那晚的情形,施一桐他在哪兒呢?也許,他就在這個看守所裡吧,至少,他還在這個城市裡吧?她想像得到,那些暴徒一定會打他,此時,他正在受刑、受苦。而跟他承受的相比,她承受的這點根本不算什麼,無足輕重。她從水泥地板上一點點爬起來,一點點坐直了。就這麼一點動彈,頭就時不時一陣頭暈地轉,令她五內翻騰,噁心想吐。她已經很久沒進什麼飲食了,四周都是天下最齷齪最骯髒的景象,足以令人一輩子不肯吃飯的。她身體裡所有的感知系統都自動封閉了。只是努力挺直了脊椎,靠坐在牆角。
看見她能動彈了,辦案人員就開始頻繁提審她。她帶著一身青紫的血痕和瘀傷,坐在審訊室裡,她一直一言不發,問什麼,都毫無回應。這回警察沒打她,只是輪番拍著桌子,最折辱最讓人失去尊嚴的那些辱罵女性的話,都對她重複罵了好幾輪,聲稱讓她在牢房裡直接被整死,死了就地火化,讓你老家的寡婦媽連收屍都收不成;要判她個十年八年,她家裡搜出來的證據,足夠她觸電無數把牢底坐穿了。從他們的威脅裡,她聽明白,他們已經去抄過家了,兩邊的家都抄了,雖然她既不是主犯也不是從犯,但明顯是脫不了干係的,就看她知道多少、吐出來多少。
她想到施一桐說過的,如果你心裡沒有了恐懼,恐懼和因為擔心死亡帶來的害怕心理,就從此遠離了你,再也碰不到你。從前,這句話聽起來很充滿哲理,卻覺得高深莫測,離人有點遠過頭了。而這一回,面對那群人獸不分的警察,看著他們四肢俱全地忙著說著毫無人倫的粗話做著傷天害理的下賤勾當,她心裡靈光一閃,陡然就領悟了那句話的涵義。她輕蔑他們,怎麼可能呢?——她想,我怎麼也不可能會去聽命於這麽一群除了暴力再沒任何含量的傢伙。 這不可能發生在我身上。
第二次提審她的時候,不在不知晝夜四面封閉的審訊室裡,而是一間正常的會客室,有沙發茶几,擺著綠色植物,朱錦被取下了手銬,被人帶著走過走廊時,窗外的陽光照在她臉上,她的眼睛痛得一下子流出眼淚。
會客室裡,她見到了一位女同事兼上級,平時工作來往很多的。還有三四個看起來是頭頭腦腦的中老年男子。女同事照例花枝招展,香氣盈盈,漂亮的臉上帶著她招牌式的可親笑容。一看見朱錦被警察帶進來,起初愣了幾秒,居然就紅了眼眶,抿著嘴要哭了。朱錦明白,自己渾身是傷,頭髮打結,面目全非的樣子嚇到她了。這女同事平時最喜歡去摸她的長長油光水滑的一把黑頭髮,在辦公室裡走過時都會順手摸一把。一起工作餐時,總是羨慕嫉妒恨地敲打她到底有什麼保養祕訣,自私到守口如瓶非要帶進棺材裡去。又要介紹她去拍洗髮水廣告,叮囑她一定要給頭髮買保險,總之,她們的話題一直圍繞著朱錦的頭髮,以及互相探討頭髮保養心得,倒也是交情篤好。@#(待續)
責任編輯:李婧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