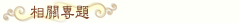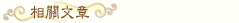一個黑暗中苟且求生的民族,一個千瘡百孔、遍地冤獄、民生凋敝的中國,一顆新星,在宦海沉浮中拼搏了半個世紀的胡耀邦終於浮出水面。
胡耀邦說:「我奉勸同志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要抓人來關。敢於大膽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監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至今沒有做過檢討。聽說他現在還在絕食。他一死就會在群眾中成為烈士,是人民心中的烈士,這種烈士是不進八寶山的」。這種寬容的思維已告別了中共階級鬥爭的觀念。
「平反葛佩琦」吹響「撥亂正反」的號角,蒙受1/4世紀冤屈的55萬右派前後摘帽。 (博訊 boxun.com)1986年,胡耀邦主持的「精神文明建設決議」,肯定了法國大革命時代平等、自由、博愛的旗幟。胡耀邦是中共的異化,這一異化是專制主義發展到「文革」頂峰後走向反面的產物。也就是在這個時期起,中國人終於享受到點滴的民主和自由的氣息。
我終於能夠作為一個大寫的「人」在共和國的土地上自由地遊弋了!
1987年夏天,我和已經考上浙江美院國畫系從而成為「兩代校友」的女兒嚴鴻穎身背帳篷睡袋,開始了考察神州大地的黃河萬里行。我們要目睹人間的一切變化,要在這自由的天空下用自己的畫筆去真切地體驗人生,表現人生。
為了證實所獲得「自由」的真實性,我們將露宿的第一站選在北京,在天安門東長安街一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門前花壇邊搭起了野營的帳篷。沒有人出來干涉我們,改革、開放使這些共和國高層次的官員們竟寬容了我們的舉動。這第一夜,我們就在武警戰士的監護下度過了此後兩個多月的考察生活中最寧靜舒適的一宿。 第二天我們向內蒙出發,經呼和浩特,溶進了烏蘭察布盟草原和白雲鄂博,腦際迴響著「藍藍的天上白雲飄,白雲下邊馬兒跑」的牧歌,在四子王旗,真正體會了「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的廣闊渺遠,領略了「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詩意。我們在草原上紮下帳篷,喝著馬奶吃著抓肉,然後從河套開始了沿著九曲黃河的考察。在烏拉特前旗,席地露營,匍伏在黃河岸畔聆聽了黃河母親的低訴。然後經烏海,翻過賀蘭山到銀川,迎著黃河落日,在黃河船夫的呐喊中迎風搏浪橫渡了黃河。我們第一次體會到了黃河的寬厚博大。過吳忠,沿途是一片貧瘠的黃土地,僅偶爾在光禿禿的山巔上發現一些窯洞和窯洞前曬著太陽的農民。這種蒼涼蠻荒原始粗朴的景觀,給我的心靈以強烈的震駭。 蘭州到了!這個中國西部最大的工業城市,似乎與我結下了不解之緣。我的青年時代似乎是在蘭州結束的,第二次是「文革」時期從新疆逃難到蘭州,毛遂自薦去畫標準像以換取返家的路費,又是在從蘭州出發的火車上降生了女兒嚴穎鴻。這已是第三次到蘭州了,往日擔驚受怕的日子巳成為記憶中的過去,現在我只是以一顆敏感而深邃的心靈去感悟人生,探索人生。從蘭州去甘南的路上,我們多了兩位同行的夥伴,在夏河,朝拜了拉蔔楞寺後,我們又去了碌曲和甘加草原,趕著犛牛過了一天西部牛仔的生活,轉一天向李卡如牧場前進。車子到達尕海吃飯時,穎鴻走進了藏民的村莊畫畫,三隻母獅般的藏獒迎面向她撲來,一件綠色大毛衣被撕成碎片,大腿也被咬了幾口。幾天後,一行五人翻山越嶺到了天池。時值6月,內地真是驕陽似火,赤日炎炎,想不到這高山之巔競下起了大雪,凍得我們直打哆嗦。 在甘南天葬場,我們目睹了天葬的奇觀。是日,天葬在日出前進行,伴隨著噴薄日出而飛起一大群矯健的禿鷲,神秘莊嚴而至,越飛越多大群降落,貪戀吞食被天葬師肢解的死屍,生命的尊嚴、生存的殘酷,生命的虛無,我難以相信這就是神聖生命和生命終極的歸宿。在西寧,建於明代的黃教大寺院金碧輝煌,鎦金瓦覆蓋的大金瓦寺在參天古木和林立佛塔映襯下顯得十分壯麗肅穆。我們在寺前石塔邊紮下帳蓬,暮色晚鐘和著喇嘛誦經聲伴隨著我們進入了一個寧靜悠遠的夢境。去鳥島途中,我們遭群狼圍堵,幾乎葬身狼腹;青海湖的浩渺深邃,碧波萬頃,風光旖旎,給了我們心靈上一種從未有過的愉悅。t 在柴達木盆地、敦煌藝術寶庫、新疆的高昌故城、火焰山、以及小涼山之巔和瀘沽湖畔都留下了我們父女的足跡…… 兩個多月的考察采風,給我們的創作帶來了豐碩的成果。1988年盛夏,我們父女倆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了《兩代人畫展》。
注重人的內心精神是東方藝術傳統的精髓。東方人習慣於把自己和自然融為一體,賦予自然以人性。而西方藝術傳統卻講究自然的精確性。西方人以自己為中心去認識世界,他們站在比較客觀的位置冷靜地去表現自然,歐洲古典主義的完美表現形式,從透視學,色彩學,結構解剖學等……把繪畫藝術納入了一個科學的框架之中。印象派大師開始尋求擺脫這種僵硬而顯得凝固了的模式,後來又從東方藝術中得到啟發,他們動搖了西方藝術模擬自然的神聖法則,開始更多地把人的內心精神注入畫面之中。從印象派至今的一多年間,西方畫壇,變化迅猛,新潮滾滾。可以說,東方藝術是西方藝術得以突變的催化劑。東西方藝術在一個世紀中產生了移位。從東方藝術精神出發,我認為繪畫是一種內心的體悟,它表現人類心靈中無邊無際又變幻莫測的精神世界。
我對真實人生的關注,超過了對抽象口號的信任。我正視現實,並表現真實存在的人生,特別是人的真實的內心世界,我的人生太壓抑,人性受扭曲,因此我更渴望通過畫筆在藝術中去宣洩,以表達不可替代的自我生命存在的意義。我在東西方藝術的夾縫裏,為尋找自己的存在而掙扎。
但我很快地我就走完了我的藝術人生!
在陽光政治缺失的中國,在鄧小平等中共強硬派元老的壓迫和盟友倒戈的情況下,1987年,胡耀邦被迫辭職。排除阻力,平反大量的冤假錯案的胡耀邦,最後卻陷入冤假錯案,無法自救。1989年4月15號,胡耀邦在中共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心臟病突發去世,引發八九「6.4」血案。
「以不變應萬變」一個不變的規律,就是中共統治每隔十年就要殺一批無辜,並且編造出這樣荒唐的理由:「殺20萬穩定20年!」,共產黨的統治至少要拿2000萬人頭來換。不允否認的現實是:這種以普通民眾的性命來穩定的政權還將繼續。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可1915年袁世凱就又稱帝,登基坐了83天的龍庭;1917年張勳又擁戴溥儀復辟皇帝;蔣介石率領國民革命軍北伐,其本質仍是獨裁;1949年後,毛就自稱「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中國人民一百多年的維新、革命、改革開放並沒有改變兩千多年的專制獨裁的本質,中國終於又變成真正鐵幕的國家!
我們從六四的血腥裏走來,承受著靈與肉的創痛!在中國,人間正義不能伸張,殺人惡魔仍揮午著屠刀!面對冥冥之中無數受害者的眼睛,如中國的奧斯維辛焚化爐烈焰烤炙著我的良知,面對黑暗與醜惡我永無寧日!我無法抹去兩幕悲壯的場景:
1989年5月23日下午,湖南省瀏陽縣小學教師余志堅、《瀏陽日報》美術編輯俞東嶽和長途汽車司機魯德成3人,用充滿顏料的雞蛋成功塗抹了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像。貼出:「五千年專制到此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的對聯。湖南三君子史無前例地挑戰神壇上的毛澤東,堪稱反獨裁、反暴君的偉大壯舉。他們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直到今天,俞東嶽仍在獄中忍受非人的折磨。
1992年5月28日,北京語言學院講師胡石根和康玉春、劉京生等組建中國第一個反對黨「中國自由民主黨」預謀在「6.4」紀念日時用模型飛機在天安門撒傳單被抓捕,判刑20、17、15年。
中國前景之黯淡,鞭韃時政、尋求國是之路通向監獄。前路漫漫,前途茫茫……
九十年代的中國北京。在像征著中華民族受盡劫難的圓明園廢墟的福緣門村,開始聚集著一群來自全國各地醉心於繪畫藝術的人,我和女兒嚴穎鴻亦加盟其中(女兒已由浙江美術學院畢業),年青的藝術家(包括詩人和歌手)從僵化的體制中掙扎出來,朝聖般地奔向藝術的麥加—–《北京圓明園藝術家村》,成為沒有工作、沒有戶口、沒有住處的先鋒藝術探索者,被世人稱之為「藝術盲流」,而踏上流浪的不歸之路。我們不是因失業、貧困、饑饉……而是為了找尋蒙龐中的藝術的聖殿,比溫飽更為神聖的超越生存的不堪明瞭的理想—–藝術與自由。
「不管世人如何評論,毀也罷,譽也罷,我們依然是堅韌地履行自己的抉擇,我們珍愛這生命的每一瞬間和每一種最寶貴的情愫,頑強地撐起理想的大樹……」對於我來說,流浪、漂泊,何嘗不是一種對人生道路,生活方式和藝術追求的選擇。(全文完)(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