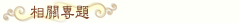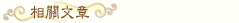【大紀元6月9日訊】天暗黑下來時,我看了一會兒書,就想早早的吹燈睡覺。這裡沒電,晚上燒油點燈,蠟燭又太貴,我燒不起,只有早早的睡覺。
剛吹滅燈,就有人來敲我的窗子。橐橐橐,地板都在抖。
「誰呀?」我問。
沒人回答,只有窗戶不停的抖。
我又劃燃火柴,點上燈,把窗戶板撐起來。一個少女的頭笑瞇瞇的伸進燈光裡,說:「你就是那個剛來的知青吧?」
我望著她,有些羞澀。那是張真正的女孩子的臉,純真中帶點頑皮。眼睛笑成了兩條縫,鼻孔上翹,臉頰上旋著兩個很深的酒窩。她看著我笑,不說話。我問急了,她才大著嗓門說:「你沒聽說過我吧。麻書隊的知青,達瓦拉姆。」
我打開門,讓她進屋來坐。她不肯,笑嘻嘻地說:「你屋裡的氣味不習慣,就站屋外。」
她身子細瘦,衣裙就顯得很長,裙角施在地上。她把手中捧的花伸進門內的燈光中,紅紅的很艷麗。她說一到隊裡就聽說我來了,就急忙趕來看我,從家中帶來的花也忘了插在瓶子裡。她問我有沒有瓶子,這花再不插在瓶子裡,就會渴死的。我在屋子裡翻找了許久,也沒有插花的瓶子。看著她滿臉的失望,我只有把茶缸裡的茶倒了,灌上水,說:「就插這裡吧。」
她說:「你用什麼喝茶呢?」
我把壺裡的茶倒進碗裡,喝了兩口,說:「用碗喝茶,又多又過癮。」
她笑了,「好吧,這花就放你這裡吧。」
她告訴我,這艷麗的小花是她媽媽種的,叫須須花,特別喜歡生長在乾燥的高原上。我看著這生得有些特別的小花,沒有闊大的葉片,細長的綠葉在花的周圍絨毛似的展開,與這些紅色的小花朵很般配。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一夜都嗅到那種帶有土腥味的花香。
她打量了一下我的屋子,說:「就你一人住這裡?怕不怕?」我說:「怕什麼?這裡除了老鼠和跳蚤,連蟑螂皮都沒看見過。」她說:「有些事你知道了,肯定會嚇得整夜睡不著覺。」
「沒什麼事會嚇住我!」我說。
她便笑,望望越來越暗的天空,說:「我得回去了。天黑盡了,保管室的門我都進不去。」我要送她,她卻不讓,說:「這裡的路我比你熟。寨子裡野狗多,你剛來,它們嗅不慣你身上的味,會把你撕成碎片的。」她朝我露了露她的虎牙,看著我驚嚇的模樣,又哈哈笑起來,一回頭,便消失在了黑暗中了。
那一夜,我眼前老晃動著她的影子,趕也趕不開。她的兩顆虎牙,一臉頑皮的笑,兩眼很深的酒窩,眉一皺鼻頭就往上翹。在夢裡,我常聽見她那很爽的笑聲,從很高的空中落下來,又緩緩地上升。那個日子,我不懂愛情,連想都不敢想。我父親和老師都說,那是黃色下流的東西。我不知道人是從那兒生下來的。十六七歲的我一直相信父母說的,我是在一個颳風下雨打大雷的夜晚,從碗櫃裡跳出來的。
第二天,我還是和兩個老阿媽曬香草。她們問我,看見麻書隊的三個女知青了嗎?我說看見了。她們說達瓦拉姆也看見了?我說看見了。她們便笑得很神秘,說達瓦拉姆也是她們的女兒。她們現在有個知青兒子,又有個知青女兒。阿意白瑪還從懷中掏出一坨糌粑,塞進我的手中,說這是專門給我捏的。我一咬,很香很甜,糌粑裡放了酥油和白糖。
我明白,她們的知青兒子就是我。
傍晚,三個拉姆都來敲我的窗戶。
我把她們讓進屋內,她們摀住嘴,說我屋內的煙很嗆。我的茶鍋內的茶還沒開,爐裡的牛糞快燒完了,一股冷煙朝外冒。我添了些牛糞,朝爐內吹著熱氣,火苗衝起來,煙卻更濃了。她們嗆得乾嚎,用圍巾摀住嘴朝屋外跑。我擦著嗆出的眼淚,說:「我燒不來這東西。」她們說,她們燒柴燒草,也燒不來牛糞。她們的柴草是支書洛熱分給她們的。
煙淡了,她們才走進屋內。茶還沒開只有坐在床邊等。燈很暗,只亮了一團,屋子的其它地方都隱在黑暗中。她們說笑了一會兒,才對我說,她們來,是想告訴我一件事,想考考我的膽量。
我說:「我的膽量夠大了,再大天空就沒有了,全包在我的手掌心了。」
坎珠拉姆的圓臉笑得更圓了,說:「你別這樣說。你知道了這事,還能睡得安穩的話,我們才真正相信你的膽量夠大。」
我滿不在乎地說:「這世界上還沒有讓我嚇得睡不著覺的事。」
達瓦拉姆細聲說:「還是別告訴他吧。這屋子很黑,看著都有害怕。」
格桑拉姆笑得滿身珠串丁丁噹噹響,說:「哈,你剛回來兩天,就知道護著他了。還不知道他心裡裝沒裝著你呢!」
達瓦拉姆的臉紅了,躲到一邊去了。我假裝聽不懂她們的話,說:「你們別找最小的欺負,看把人家說得快哭了。」
坎珠拉姆還是一臉的笑,說:「你倆的事,我們想管也管不了。我們只想給你講講發生在這屋內的事,免得你住在這裡,什麼事也不知道,像個傻瓜似的。」
一年前,這屋內發生了一件慘烈事。我聽她們講這件事時,心裡一點也不感到恐怖,鼻腔有些發酸,很想痛痛快快地掉幾滴眼淚。
我能感覺到屋內的黑暗深處,躲著什麼東西正尖起耳朵靜靜地聽。
一年前這屋裡曾住著三個老知青,是從很遠很遠的重慶插隊到這裡的。他們的父輩都是到過這裡的老紅軍。他們來這裡,就是想在父輩幹過革命的地方鍛煉自己。當然,這裡知青少,讀書、招工招干也容易。
他們兩男一女,男的英俊有才,一個會畫畫,會一手漂亮的木匠活;一個會寫文章,毛筆字寫得瀟瀟灑灑,常常躲在屋角嘰哩呱啦說俄語。女的嬌小,有些像達瓦拉姆,不愛說話不愛笑,心卻很靈,兩個男知青的漂亮毛衣,全是她織的……
他們住在屋內,丁丁丁,鏵犁敲響時,他們上工。下工後他們就呆在這屋內,很少出門。一年又一年……
「聽明白了吧?」坎珠拉姆故意停頓了一下,狡猾地望著我,說:「兩男一女住在這屋內,會發生什麼事?」我不明白地搖搖頭,她便笑,格桑拉姆和達瓦拉姆也跟著笑,她們很得意自己是明白人。坎珠拉姆埋怨我說:「你真的是個沒長醒的娃娃。說給你聽,你別嚇著。兩男一女坐一間屋子,會發生三角戀愛,就像玩傳皮球,你傳給我,我傳給他,他又傳給你。這是三個人的遊戲,一點也不好玩。」
五年過去了,他們終於等來了回城指標,三個,一為招工,一為招生,一為招干。他們商量後,女的去讀書,會木匠的正好去工廠做車工,會寫字的就去機關當幹部。填好表後,他們買來很多酒,把喂的下蛋雞全殺了,熱熱鬧鬧地醉到半夜。女的受不了啦,臉一紅就大口大口地吐,血都嘔了出來。他們為她灌瞭解酒的醋,她緩過氣來,才羞怯地說,她也許不能走了,她怕去醫院體檢。兩個男的勸解說,喝了點酒算不了什麼大毛病,她身體健壯,當女飛行員都行。她說什麼也不去,只是摀住臉哭。在兩個男人可憐巴巴的安慰聲中,她才羞羞答答地說了實話。她已經有三個多月沒來例假了,可能懷上了。兩個男人都慌了,抱著頭不知所措。這事能怪誰?孩子又是誰的?他倆都說不清楚。這樣的事又是從來沒遇到過的,不可能大男人走了,把一個懷著他們孩子的女人扔到這裡不管。
屋內很黑,燈全燃盡了,只有爐內的牛糞火燃得很惡,像充了血的眼球。會木匠的男人說,他想把這件事處理好。他母親是婦產醫生,他曾翻過母親的專業書,懂得一些那方面的知識。
他用酒洗了手,又把一隻勺子放在火上燒,放在酒中浸浸,叫來會寫字的男人找來繩子捆住女人的手腳,把手在火上烤烤,就動手了。
屋內傳來慘烈的叫聲,把許多人家的睡夢都吵醒了。他把枕巾塞進女人的嘴裡,叫她別喊。
坎珠拉姆停住不講了,看看癡癡呆呆地聽她講的我,又看看摀住耳朵什麼也不想聽的達瓦拉姆,忍不住笑了,說:「下面發生的事我就不講了,你們自己明白就行了。」
我說:「我一點也不明白。」
她說:「不明白,我更不會講。那是黃色的東西,說出來會腐蝕你純潔的心靈。」
她把中間那部分跳了過去,跳到那女人昏死在地上,滿屋是噴射出的血。隊長多吉和文書老劉撞開了門,被這血淋淋的景象驚呆了。他們朝兩個嚇傻了的男人大吼一聲:「還不快點她上醫院!」
兩個男人才背起血淋淋的女人,朝醫院瘋跑。
她由於流血過多,半路上便斷了氣。
兩個男人憋著滿肚子的悲傷,回到冷冰冰的屋內。他們先是抱頭歎息,說自己無能,沒有保護好女人。又互相埋怨,出言相譏,眼內滿是仇恨。後來,兩人便破口大罵,拳頭相毆,在兩人都被揍得鼻青臉腫時,一人拿起了木工的斧頭,一人舉起了切菜的鋼刀,瘋狂地砍殺起來。最後,木匠知青的斧頭狠狠地釘在了寫字知青的頭頂上。血像噴泉似的從寫字知青的頭上射出來,像根木樁子栽倒在地上。
木匠知青心慌了,在屋內東躲西藏都不放心,他眼前都是滾滾湧來的黑霧,血腥味嗆得他喘不氣。他絕望了,用一根牛毛繩把自己掛在了屋樑上……
事情就像一陣冷風從屋角刮來又刮去,屋內似乎更黑更暗,暗得能聽見所有人的心臟有節奏地跳動。糞煙早已飄盡,紅紅的炭火安靜地在茶鍋下燃燒。茶香味隨著白霧飄散開來,我似乎嗅到了那股嗆人的腥味,端碗的手也在顫抖。
坎珠拉姆默默地吞茶,抬起那雙很詭的眼睛看看我,又看看達瓦拉姆,說:「我的故事嚇著你們了吧?」格桑拉姆說:「看看,嚇得他不敢在這屋子內住了。」我哈地一聲,胸脯一挺,說:「嚇我?算了吧。就是把那幾個死人搬到我的床鋪上,我也敢和他們一個被窩睡。」
達瓦拉姆驚得伸了伸舌頭。
坎珠拉姆把茶喝完,說:「好了,故事也講完了,我們也該走了。祝你睡個好覺。」
她們出門時,都格格格笑起來。
那一夜,我點了整整一晚上的油燈,把滿滿一瓶煤油燃干燃盡,只剩一絲噴著濃重氣味的黑煙。我獨坐在冰冷的床頭,朝黑森森的牆角東看西看,什麼地方發出輕微的響動,我的心內都會猛地一抽,背脊冷得僵硬。我在地上、茶桌上、碗筷上、甚至我的被窩內,都能嗅到濃濃的血腥味。這屋子我再也不敢住了,天亮後就去找老劉,換間屋子住。
可一想坎珠拉姆那張帶著嘲笑的臉,我的脖子又硬了。我一個大男人不會讓幾個女人的故事嚇住,那樣我會沒臉皮見亞麻書的鄉親們的。不換,就住這裡,我倒想看看,那幾個死鬼會把我怎麼樣。
夜漸漸深了,寒冷了。我緊緊抱著被子,身子變輕了,如一根細草飄進了夢裡……
第二天上工,坎珠拉姆看著我笑,說我肯定哭了一夜,不然眼睛不會這麼紅腫。我說,是早上生火柴濕,讓濃煙熏出的。
午後,風很大,刮得天空陰慘慘的,像要下雨的樣子。我與兩個老阿媽在風中搶收曬得半干的香草,風捲著細沙直往眼內灌。兩個老阿媽叫我回去睡一覺再來,說我幹著活都在打盹,肯定是這兩天太累了。
見我順著獨木梯走了,便說:「小洛,下雨就不要來了,下雨我們都會回家去烤火的。」
我應著,望望天,雲團越來越黑,冷颼颼的風中都能嗅到雨的腥味。
在我家的門前,達瓦拉姆靠牆站在那兒。她一手抱著琴盒,一手提著裝東西的網兜,伸長脖子在那裡東看西看。見我來了,便高興得笑了,說:「我等了你半天了。」我奇怪,說:「等我有什麼急事?工也不出?」她說:「公社要組織文藝宣傳隊,叫我留在家中練琴。在我們住的那兒練琴不太方便,坎珠拉姆嫌琴聲太吵,我就上你這兒來了。」
我開了門,讓她進屋。她問我吃飯了沒有,我說還沒吃。她把網兜打開,說:「正好,我帶了點麵粉,給你做麵條。」
她從水缸中舀來一銅瓢水,把麵粉倒在盆裡,挽起袖子細細的手伸進盆裡和面。我便在爐中添了幾塊干牛糞,把火心掏空,使火燃得更旺。
她望著我,鼻尖上沾滿了白色的麵粉。她想起了什麼,撲哧一笑,說:「你昨晚肯定嚇得一夜都沒睡好覺。」
我脖子一硬,說:「有什麼好嚇人的,不就是死了幾個人嘛!我睡得好好的,連夢都沒做,眼一閉就大天亮了。」
她埋頭揉面,低聲說:「對了,死人哪能嚇得了活人的,只有活人嚇活人。」
我說:「那三個老知青也太可憐了。為這麼點事殺來殺去,心胸也太狹窄了。」
她抬起頭,窗外有一絲陽光射在她的臉上,眼內閃著一團金色。她說:「他們就埋在對面的山坡上,三個人合葬一個坑。當地人都不興埋入泥土,好好的人死後,都興天葬、水葬和火葬,只有凶死的人和犯了重罪的人才埋入土中。所以,那山坡上的草長得很好,隊裡的牛羊很少趕到那裡去吃草。寨裡人說,牛羊吃了那地方的草,會患一種怪病死掉。真的,我親眼看見一半歲大的牛死在那裡,口中銜著半根吃剩的草,怪怪的。」
後來,我去了那個土坡,看見了那座讓厚厚的雜草嚴嚴實實淹沒著的知青墓,心裡有種難以說出的滋味。人的命運真如草一般,可以豐盛也可以衰敗,誰也說不清楚。以前,我是個依靠父母的乳汁長大的,不知生活中還有那麼多怪怪的滋味的學生娃,無憂無慮生活在藍天白雲下。如今,我站在這片屬於青藏高原的黑土地上,要成長為一個地地道道的「洛巴(農夫)」,將來會是怎樣的?會像這高原陽光一般明潔清亮嗎?看著這座巨大的墳墓,恐懼爬滿了我的心內。未來的不可知,讓人想起就生滿了恐怖。那一天,我學會了沉默,模樣深沉使別人看起我來都產生老謀深算的錯覺。其實,我心內空空如也,連一絲東西都不願裝下。
離開那兒時,我指著荒草萋萋的墳墓說:「你們都把眼睛睜大看我吧。看清楚點,我是新來的,不會走你們的老路,不會讓人用輕蔑的眼光看著我在這裡樹起一座墳墓。我會活得比你們好,我有自己的生活目標,我會做自己的事,會克制自己的情慾,永遠也不會衝動。你們把眼睛睜大一些吧,從現在開始,看著我從這裡走出去,走出一條新路來吧!」
不過,我發現那裡的花比其它地方的花開得都要旺,一串一串的,五顏六色鑲在草灘上。花朵很小,花瓣珠子似的盤在花蕊上,很像小小的向日葵。
達瓦拉姆的面塊煮好了,她拿瓢在鍋裡一攪,一股鮮香的氣味便飄散開來。她舀了一大碗給我,說:「嘗嘗,味道如何?」我嚼了一大口,故意皺著眉頭裝出很難受的模樣,嘴裡咿咿嗚嗚地叫著。她擔心死了,瞪大吃驚的眼睛望著我問:「怎麼了?很難吃吧?」我僵起舌頭含混不清地答著,她端過我的碗,也嘗了一口,搖搖頭問:「怎麼啦?」
我卡著脖子,做出憋氣難受的模樣,看她急得快要哭了,淚珠在眼眶內滾動著,才緩過氣,歎息一聲,笑著說:「天呀,太好吃了!舌頭都快讓我吞進肚皮中去了。」
她哇地叫了一聲,衝過來,拳頭在我背上擂著,尖叫著說:「你嚇死我了,嚇死我了!」
我一面笑一面躲閃,開心極了。我從小到大從沒有這麼開心過。上了中學,女孩子在我們的眼中,都成了會吃人肉老虎,躲避得越遠越好。那年月,愛的幼芽根本不可能萌發,那是黃色的東西,是比口痰更讓人噁心的污穢物。來到這裡,我卻感到多麼的自由。女孩子是那麼的可愛和有趣。也在那一天,我吃了達瓦拉姆香噴噴的面塊後,我的細嫩的嗓音發生了吃驚的變化,不再有童音的清脆,稍一用力,公雞的打鳴聲便飛了出來,引起周圍人哈哈大笑。
我仍然毫無顧忌地用這難聽的聲音說話,說我剛學會的藏語。
吃完麵塊,達瓦拉姆把鍋碗收拾得乾乾淨淨,坐下來,看著屋外一地的陽光,說:「我想拉琴。」
我說:「拉吧,我喜歡聽別人拉琴。」
她把琴從盒中取出來,是一把舊得看不出漆色的琴。她調著琴音,說:「琴是我爸用過的,他在州文工團拉過琴。我爸教我拉大提琴,我不喜歡拉那笨重的傢伙,就偷著拉我爸用過琴。下鄉時,我把它也偷來了,反正我爸的文工團也解散了,他們也用不著這個了。」
她又問我:「你會不會拉琴?」
我說:「不會。我爸會,他拉的是二胡。不過,他拉琴的模樣比拉出聲音更精采。他一拉二胡,眼睛就瞇上了,眉頭皺成疙瘩,像在忍受什麼難言的痛苦。嘴唇隨著琴弦的拉扯左歪右咧。我很小的時候,就愛蹲在他的腿下,奇怪地看著他的怪相。」我朝達瓦拉姆做了個我爸拉琴的模樣,瞇眼皺眉,嘴唇左歪右咧。她咯咯地笑了,笑得前仰後合,喘不過氣,說我真會逗人。
達瓦拉姆拉琴的姿勢很美,她站在我的暗黑的屋子和明亮的窗戶之間,那反差強烈的剪影簡直美極了,像我曾經見過的一幅音樂女神浮雕的照片。少年的我第一次感覺到了少女身材的美妙,我呆在暗處,張著嘴哈出粗氣,有些癡呆,腦子裡一片空白,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了。
琴聲還沒響起,美妙的音樂聲已從她的身上傳出了。
她的整個身心都沉浸在了音樂裡,她已看不見我的存在了。她的琴聲緩緩的流淌出來,是細小的山泉,清冽的帶著雪山的香氣,淌著飄著,流進一汪藍得透明的高山湖泊裡。她在湖面靜靜地漂著,枕著一朵白得耀眼的雲團,她的黑髮與青綠的水草一起蕩著,串串五顏六色的小魚在她的髮絲間舞動,那就是音符,就是節拍,就是重音與低音……。平靜的湖面沒一絲波紋,靜得如修煉多年的僧侶的心,靜得讓人擔心她的脆弱與粉碎。
那是我第一次用心去感覺音樂,我終於看見了,音樂是一個美得讓人不忍心眨眨眼睛的實體。是要你小小心心去愛惜的易破碎的泥塑,是比野花更能讓人感覺到大自然濃郁香氣的生物……。達瓦拉姆奏完了,我看見她的臉頰讓淚浸滿了。她說,這是她爸爸創作的曲子,叫《靜野聖湖》。她一拉這曲子,心裡就激動。
我說:「我也是第一次聽到這麼美的曲子。」
她說:「還有更美的。不過,不是我爸作的,是一個叫舒伯特的外國人作的,叫《藍色的多腦河》。」她又拉,抒情的曲子便滿屋流淌。窗前不知什麼時候圍滿了人,都露出一種笑臉。達瓦拉姆看看窗前,曲子一轉,《北京的金山上》便跳了出來,窗前的人想也不想,便和著曲子唱起來。
美妙的音樂聲,便讓一股突來的狂風刮跑了。
風刮過後,又是滿窗的陽光。
達瓦拉姆把琴裝進盒子,指指窗外說:「看看,雨停了,天也晴了。我們都該出工了。」
亞書隊的鐵鏵犁和麻書隊的牛皮鼓同時響起,窗前的人呼啦走散了。
我關上窗戶,說要把這滿屋的音樂關得緊緊的,一個也不讓它們逃掉。(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