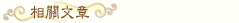過去幾個月,我聽過太多故事,恐怖的、悲傷的都有。屍袋拉鍊被拉開時我就站在旁邊,我很清楚事實裡大量摻雜著虛構的想像。可是那些故事、說故事的人,以及我們祝福過的遺骸,全部都出自「我方」的觀點。聽見「另一方」的事從個人嘴裡說出,這還是頭一遭。當然劫機者的遺骸會跟受害者的混雜在一起,只是我沒想到罷了,因為我只顧著撫慰「我方」。
我問魯迪他們怎麼知道那是「他們」當中的一個,他說他也不清楚,不過他猜可能跟那具遺體被發現的位置,還有它和飛機的局部構造非常接近有關。我想像這具遺體,或者殘骸,被一群或許有朋友罹難的紐約消防員和警察、港務警局官員和建築工人團團圍住的畫面。
「你也在場?」我問。
「是啊。」
「發現那是劫機者之一時,大夥兒做了什麼呢?朝遺體吐口水或是用什麼方式侮辱它嗎?」不管傳言是真是假,我想像它應該會引爆不小的激烈情緒。
想也沒想,魯迪搖了搖頭。
「不⋯⋯沒這回事。我們懷著敬意處理這具遺骸,和處理其他遺骸沒兩樣。」
我很吃驚,完全沒料到他會這麼說。他的反應之率真、語氣之誠懇,在在令人驚嘆。我對他說,我非常吃驚,而且真心為當時在場的所有人,包括他在內,感到驕傲。
他用一雙清澈的眼睛看著我,理所當然地回說:「我們只是互相提醒:喂,記住,這是某人的兒子,現在也還是某人的兒子。」
我知道我聽見了神聖的話語。
將近凌晨兩點,我結束和魯迪的對話,走出活動拖車去透透氣。還沒有遺骸送進來,不過我還是把我的手機號碼留在牆上,以備不時之需。這種情況很正常。
如果整晚沒事,停屍間的牧師可以在現場到處走動,為其他人打氣。我決定前往人稱第十消防站(Ten House)——或10─10,也就是第十幫浦車隊、第十雲梯車隊——的消防大隊。
這個消防站就位在災變現場周邊,也是最接近世貿中心的消防站。一聽見飛機撞擊北塔的聲音,幾個值班的人員衝向窗口,發現大樓起火燃燒。幾小時不到,他們當中有五個人喪生。之後這個消防站嚴重受損,如今作為儲存裝備和其它物品之用。
輪班時,我經常到那裡借用浴室,或者站在屋頂眺望整片災變現場。站內氣氛有點陰森。即便只是我胡亂想像那些人的幽魂在其中流連,我仍能對他們的靈魂產生共鳴。
一邊走著,我猛然想到,這晚的災變現場好像不太一樣。什麼東西不見了,但又想不起到底是什麼。就在到達第十消防站之前,我想起是狗兒們。我好想念以前在這兒出現過的搜救犬和醫療犬。也許因為冷天加上搜索不到殘骸,更別提我是輪值夜班,因此很難看見牠們。
對這裡的每個人——包括我——來說,牠們的存在可說是一大安慰。搖晃的尾巴可以如此地振奮人心,實在神奇。
當找到存活者的期盼轉換為找到殘骸的期待,就連幾隻搜救犬都受到了影響。日復一日,以及漫長的夜裡,狗兒們不斷搜尋著生命跡象。搜索落空的持續挫敗使得牠們精神不振,你可以從牠們的疲倦眼神和姿態中看出來。
有時候,為了激勵牠們,建築工人或消防員會把某個同事藏在碎石裡,然後讓訓犬員過來。聞出氣味的狗會開始興奮地挖掘被淺埋起來的人。當「救援」完成,所有人一起歡呼,狗兒的精神就又來了,尾巴猛搖,眼睛發亮,你可以看出某種內在的火焰重新點燃。
這份對狗兒的憐憫也讓在場的人重振起精神,提醒他們自己的任務並未失敗。有勇氣每天到這兒來,竭盡所能付出,而仍然能夠關懷別人,光這點就是一種成功。我們可以繼續盼望——不是期待找到生還者,而是希望自己能活下去。
我登上通往第十消防站屋頂的階梯,一邊沉思著狗兒和魯迪告訴我的那些事。我一踏出去,驚訝地發現外頭站著一個女人,一個看來大約四十七、八歲的救護技術員。她靠在圍牆邊緣,金色直髮飄在腦後,讓我想起船頭的人頭雕像:神祕、堅毅,有一張看不出喜怒的臉龐。
我正想離開,因為我不想打擾她獨處;可是她正好回頭看見我。當我們目光相遇,她用一種親切但又戒慎的表情向我招呼。我在世貿現場見多了類似的表情,因此並不以為意。我知道這是疲憊、憂傷,加上極力想壓制自己情緒的結果。
我們並肩站在那裡,凝視著下方不曾停歇的工作狀況。從我們的有利位置,卡車的鏗隆鏗隆聲變得微弱了些,被夜空的消音板吸收了。能夠抽離忙碌和噪音真是一大快慰。我們就像兩隻找到一處高高的窗臺歇腳的鳥兒。
這位救護技術員告訴我,她正好在第二棟樓倒塌前到達這裡。
「簡直像身在地獄,」她說。
「眼前一片黑,根本不能呼吸。我和我同事在混亂和黑暗中走失了,你可以聽見腳底下有人尖叫,可是什麼都看不見,真是太可怕了。我不斷想著我的五個孩子,而且正打算離開雙塔。起初我有點猶豫,心想我應該先找到我的工作夥伴,可是我繼續往前走。直到當天深夜我才聽說他順利逃出去了。要是當時我回去找他,現在或許不在這裡了。要是他回去找我,他的下場也一樣。他嚇得一直不敢回到這兒來⋯⋯可是我每個月總要來兩、三次。」
「妳都如何面對那些影像、那些記憶?」我問。
「我也不知道。」她說:「我想我只能把心放在孩子身上,在這裡盡點力幫忙。」
「我願意把生命交到這個女人手中。」我心想。
她生養了五個孩子,曾經和死亡打過照面,如今又回來賣命。有好一陣子,我們靜靜站著,兩個聯合起來抵抗悲慘處境的母親。沒有交談半句,只是讓寒風吹襲我們的頭髮。她的臉輪廓鮮明而美麗,在我眼中猶如一個站在崗位上守護著這片災變現場的天使。
「我們還是回去幹活吧!」她說:「有緣再見了。」
「但願如此。」我說著和她握手。
「好好照料孩子們。他們很幸運有一個這麼勇敢的媽媽。」
「妳也一樣。」
她笑笑,然而眼裡的光迅速黯淡下來,像是關上了簾子。我不知道她是退縮回去以便能繼續撐下去,還是試圖把那些可怕影像隔絕在外。關於她這部分的故事,我恐怕永遠都不會知道。
下了階梯,我們分頭走開。我回停屍間,她隱入夜色中。
我發現自己在每次與人互動之後總是習慣性地小聲禱告。我喃喃默念著無語的祈願——為了什麼?為這些男男女女的平安,為他們的親人,為所有那些再也不能迎接親人回家的家庭。
我禱告,為了讓自己能繼續走下去。
我祈求能擁有智慧,能說出貼切的話語,以便面對下一個需要安慰的人。
我祈求自己不會忘了這些人的面孔。我將它們一一編織,像禱告披肩那樣圍在肩頭。
我邁開大步迅速走回拖車,彷彿這樣便能逃離寒風似地。一進到裡頭,我立刻和一位緊急醫療服務(EMS)技術士(lieutenant)四目交接。他是個灰髮、有張娃娃臉的矮壯男子。一雙藍眼睛儘管充滿哀傷,卻十分親切。
我在他身上發現我在這裡見過無數次的東西:想要訴說自身故事的一種羞澀的渴望。除非他們開口說出來,別人往往不知道該如何看待他們。找我或其他牧師聊聊,有時未嘗不是一種探究自己情感的方式。單靠自己這麼做或許會有點可怕。有時候這也是一種自白的方式。我不確定這位技術士腦子裡想些什麼,不過我看得出來他很想談談。
我們走到一個較隱密的角落,雖說事實上並不需要這麼做。目前拖車內只有另外兩個睏倦的人,而且似乎正在打盹。
我們先閒聊了一下彼此的家和親人。事情通常都是這麼進行的。我們必須先透過一些合情合理、平凡穩當的事物搭起關係,然後才會冒險涉入這陣子的各種驚駭和恐怖話題。
他告訴我有關他的兩個孩子的事,一男一女。描述他的兒子時,他開始眼泛淚光,喉嚨哽咽起來。
「他實在是貼心得不得了。」技術士說:「我也說不清楚,總之他是可愛又仁慈的孩子。我女兒也很棒,不過是個麻煩精。」
他大笑,搖了搖頭。
我感覺他在他兒子身上感受到某種脆弱性,激發了他的保護慾。也許他渴望能保護兒子免於遭受許多人子面臨的危險,讓人子葬身在這停屍間外面、葬身在古今所有戰場上的那種危險。如果他保護得了他兒子,或許也就能找到,並且保護九一一那天遭到摧殘的,存在他內心的那個孩子。
技術士低頭抹著淚水,接著開始談起當天他也在這裡。
「妳絕對無法想像那種狀況,人面臨的艱難抉擇,那種驚恐。有個朋友告訴我,當時他和他的工作夥伴剛抬著一個女人走下好幾層樓梯。她已經陷入昏迷,看來早就斷氣了。他們才剛走出大樓,它就開始倒下來了。妳可知道他們怎麼做?」
他問,來回搜索著我的眼睛。
「他們把她放下,開始沒命地跑。他們非把她留下不可,因為他們只有幾秒鐘時間。要是繼續抬著她,他們肯定全部沒命。可憐的女人。到現在我朋友還難過得要命,他老是想起她。可是,要知道,他有四個孩子,他不得不做個抉擇。但他良心上過不去。為什麼老天要逼人做這種決定呢?」
「沒人知道在那種情況下自己會怎麼做,」我輕聲說:「除非自己遇上了,而且誰都沒有資格批判別人在那種生死關頭可能會做的事。」
「妳知道讓我最難受的是什麼嗎?粉塵。從鋪天蓋地的粉塵中走過,我們很清楚我們也從人的骨灰中走過。我身上蓋滿了,蓋滿了別人的骨灰。」
技術士哭了起來。他垂下頭,一手捂著臉,將淚水嘩啦嘩啦倒入看來像是匯集了集體傷痛的無底巨杯的掌心。
「對不起。」
他說,揉著眼睛。
「這是我事發到現在第一次哭。我沒事的。」
憂傷壓在他壯碩的肩上。他會忍住…….可是他真的會沒事嗎?我們當中有誰會真的沒事?儘管機會不大,但他的某些特質讓我仍然對他抱有希望——他的勇氣,他的正直,他那溫柔的憂傷。我為他的小兒子和女兒默念了一段感恩詞,然後為他內心的赤子——他暫時遺失了的那個部分——祈禱。
當然,我們決定到這兒來都是因為熱切地想要盡點力。但要是有恐怖的影像縈繞不去呢?要是必須做出沒有回頭路的抉擇呢?站在技術士身邊,我將手放在他肩頭。我感覺得到天使翅膀在他夾克底下翩然鼓動。他可知道它們的存在?他可曾想到,他穿著行走的鞋子是上帝的鞋?
「繼續說吧!」我心想:「繼續訴說你的故事,一直說到你的負荷消失,一直說到那些骨灰成了雪花落下,有如寬恕,一片片,在獨一無二的完美裡,消融於無形。」
等我轉進我家那條街、把車開進車道時,冬陽已漸漸上升。成排的房舍看來已經不再像嬰兒床,它們是將我們緊緊托住、讓我們不至於散落到冰凍草地上的骨架。我需要再度回到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的身體,回到我自己的人生。我好想,但不知怎地有些猶豫。我知道自己既疲倦又亢奮,不斷想著我似乎遺忘了什麼。也許是我的一部分,而我必須把它召喚回來。也許我想太多了。
我打開門,屋內一片寂靜。我們的鬥牛犬賽奇正肚子朝上,呼嚕呼嚕睡得香甜。我走進來時,牠連動都沒動一下。好個盡責的看門犬。拆開的聖誕禮物散置在地板上,感覺似乎也正沉沉睡著。只有那棵樹——張開綠色臂膀,渾身松香——仍然醒著向我道早安。
我輕手輕腳走上樓梯,進了女兒的房間。我在她身邊躺下,將鼻子湊近她的臉頰。她身上有種熱麵包的味道。
「媽咪,妳回來了!」
她睡眼矇矓地說,身體偎了過來。
「是啊,親愛的,我回家了。」我悄聲說:「我回家了。」
我閉上眼睛,將這晚的種種一切用簾子隔開。在簾子的那側,市中心的機具仍然隆隆運轉,精神抖擻的工人來接手疲憊同事的班。我無法答應女兒這是我最後一次輪值。新年快到了,還有太多工作要做。我不必再去,我隨時可以說不。可是我把自己的一些碎片留在了世貿災變現場,這會兒帶著別人的碎片。
除非整個工作完成,我怎麼也無法把自己完整拼湊起來,而且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置這些別人的殘片。我選擇了一幅圖案細緻繁複、部件纖弱的馬賽克拼圖。縱使最終的構圖還不明晰,我知道所有的碎片都在那裡。同樣的光從藍色、白色的碎片折射出來,無論是光滑或粗糙。它照亮空白的部分,填補了空隙,直到下一個碎片被發現為止。
目前,我正站在大片深達膝蓋的彩色玻璃碎片中。也許,總有一天我可以退後一步欣賞。而我期待看見的是一股更加深化、而非裂解的信心,不管是對於人性、上帝,或者我所做的抉擇。◇(節錄完)
——節錄自《讓光照亮你的心》/聯經出版公司
責任編輯:李昀
點閱【書摘:讓光照亮你的心】系列文章。